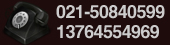雕塑家潘鹤访谈(摘自南方都市报)

谈艺録20 潘鹤 别名潘思伟,著名雕塑家,1925年生于广州,籍贯广东南海。曾师从岭南派画家学国画。后在香港、澳门等地从事肖像雕塑。1949年后进入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学习。历任广州美术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美协常务理事、广东分会副主席和全国城市雕塑艺委会副主任。潘鹤致力于雕塑艺术6 4年,从事美术教育4 5年。创作了大量经典雕塑作品,如《深圳开荒牛》、《艰苦岁月》等。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 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90岁的潘鹤,虽然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仍不改“猛男”本色,不仅在回忆自己作品时,如数家珍;论及当下的中国雕塑界,更是直言不讳。 大部分人对潘鹤或许并不熟悉,但一定见过他的作品。从代表深圳精神的《开荒牛》,到珠海标志的《珠海渔女》,又或是广州海珠广场的《广州解放纪念像》,竖立在内蒙的“昭君”,华清池边出浴的“贵妃”,再有像教科书上出现的雕塑《艰苦岁月》、《洪秀全》等等,都是潘鹤的作品。 这可能正是潘鹤在1980年代积极倡导室外雕塑的原因之一:能够让更多的,不同代际的人都能欣赏到雕塑之美。在潘鹤看来,这也正是雕塑异于,或者说优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原因。得益于潘鹤及其同辈雕塑家的努力,使得中国室外雕塑进入了蓬勃发展期。不过,面对时下中国出现的室外雕塑乱象,做工低下,毫无艺术美感可言的雕塑大量出现,潘鹤也是一筹莫展。 我走雕塑这条路是爱情的功劳 我在广州经常给我表妹写信,她在信里一直鼓励我继续美术创作,这对我影响非常大。 南都:你现在还有在做创作吗? 潘鹤:现在,只有真正能打动我的活儿,我有话要说我才接,打动不了我的我就不接。现在有很多做雕塑的,完全是为名为利,唯利是图,我很看不顺眼。都是在说“钱钱钱”,讨厌得不得了。我不愿意浮在水面上,和这些人同流合污。以前浮在水面的是英雄,现在浮在水面的是狗熊。过去我常说,我们希望水涨船高,把英雄浮上水面。现在是打倒别人提高自己,水落石出,狗熊浮到水面,英雄倒在下面了。 南都:“有话要说”该怎么理解呢? 潘鹤:“有话要说”,如果我把这些话白纸黑字写下来,很容易被人抓住痛脚。但雕塑不一样,你看到我做的东西,觉得好像是某个意思,但我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在里面还有我自己想说的东西。我每件作品都有这样的构思,无论是《艰苦岁月》,还是《开荒牛》,又或者是《珠海渔女》,这些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有话要说”。我是很可怜文学家,有些文学家也有跟我一样的思想,但如果你话说不清楚,别人就看不出来,说清楚了,又容易被人抓住痛脚。绘画也有这个问题,太抽象别人看不出来,不抽象又让人抓住。 我做《开荒牛》的时候,全部人都批评我:我们是特区,怎么让我们做牛做马?除了当时深圳的一把手,其他人全部反对这个雕塑。《珠海渔女》也是一样,当时很多人说“我们是特区啊,要男人站起来,要发奋图强,门户打开,你做女人雕塑干什么?”骂我也是骂得要命。但是最后还是我胜利了。 南都:现在好像把艺术等同于拍卖和收藏了。 潘鹤:我自己虽然早就看破红尘了,但有机会我就会骂他们,讽刺他们,这些东西都没逃过我的眼睛。我写过一首打油词———“滚滚潮流东逝水,又岂料浪花淘剩狗熊,弄虚作假终成空。青山依旧在,管它垃圾浮。庭前落叶循环事,惯看春夏秋冬。一瓶红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所有那些很有名的艺术家,都是浮在水面,很快就消逝了,但是青山依旧在,它是不可能被冲垮的。我就写这样一首词来讽刺当下,骂现在那些人。人们都为了钱生存,都不是为了正义生存。风格也不是人格的表达了,而是流行什么风格,就是什么风格。我的感觉是,整个文艺界是落叶时代,但春天来了一样还是会发芽,还是有希望的。 南都:你当初是怎么样开始走雕塑这条路? 潘鹤:完全是爱情的功劳。我十几岁到香港,当时很喜欢画画,那时候我和表妹谈恋爱。她也经常夸我画得很好,她算是最早欣赏我的人,所以我特别高兴,一直在画。后来,日本攻占了香港,一下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报纸、广播,也没有书籍、朋友。但我发现自己有话要说,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写日记,也特别迷文学,当时还写过几百首诗。 现在的人老觉得,搞艺术是很有钱的,当时刚好相反,人们最瞧不起的就是搞艺术的。我跟表妹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她父母坚决反对,非逼着我立即改行学做生意。我爸妈也不同意我们结婚,他们也觉得搞艺术是没前途的,我以后根本养不起我表妹。但我的性格是,你越打我,我就越反抗;如果你赞赏我,我反而就软了。所以我坚决不改行,就是要搞艺术。 不久以后,我就离开了香港逃难回了广州。当时广州早已沦陷,我在广州就经常给我表妹写信,她在信里一直鼓励我继续美术创作,这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当时也特别想她,但没法表达自己的感情,于是我就开始画她的肖像。我当时用粉彩画她,画完以后想去亲下她,结果那些粉彩全沾到我嘴上了。我思来想去,究竟什么材料才不会掉色呢?这时才开始做雕塑了。 南都:你做雕塑完全是自学的? 潘鹤:我没有老师。当时在香港、广州和佛山也根本没有一个艺术家,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生存。当时也没人敢去写生,因为日本人会抓写生的人,觉得你肯定是地下分子,在记录情报。我当时是做我表妹的塑像,是做我心爱的东西,所以也特别用心,这些作品很多都留下来了。我一生经历过三十八次政治运动,父母都劝我不要从事艺术,我的爱情也因为艺术夭折了,但我就是这样,越骂我,我越顽固。 我当时住在广州首富的家里,他特别喜欢我,后来他又用各种办法保护我到了澳门。当时澳门也集结了一批大艺术家,像徐悲鸿、高剑父当时都在澳门,但不谦虚地说,当时他们在澳门的影响力根本比不上我,不仅广州首富,还有澳门首富、香港首富都认我做“契仔”(干儿子),都非常喜欢我做的东西。 我也敢说,当时除了我表妹,没有任何人对我有过什么影响,我也看不起他们。当时我父亲想要我找个老师,我日记里直接就写:谁配做我的老师?不要说中国,全世界当代没有一个配做我的老师,除非是米开朗琪罗复生。当时我是非常狂妄的。 前50年是我的艺术积累期 前50年是我的艺术积累期,到后30年我才真正爆发。 南都:在“文革”以前,你的作品似乎并不多,比较有名的应该是《艰苦岁月》和《当我长大的时候》? 潘鹤:“文革”前,我的作品很少,当时也是整天忙着下乡土改,搞民主改革等等,真正创作的时间并不多。谈到《艰苦岁月》,这个作品其实是不断变化的,最早的原型是我在1946年做的。当时的想法是,那个小孩是我,吹笛子的大人是这个社会,我想把我的心声跟社会说,但社会却不理我,说的是我自己的苦闷。10年以后,我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吹笛子的人是我,听的人则是这个社会。《当我长大的时候》是我在1952年的作品,当时毛泽东看中了这个作品,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小孩在讲话,老师看到,心里很舒服,因为她能把自己的思想和人格传到下一代了。 南都:说回到《艰苦岁月》,可以说是你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了,能不能聊一聊创作的过程? 潘鹤:《艰苦岁月》创作于1956年。当年,军委总政治部为了庆祝建军三十周年筹备美展,向全国各地美术家征集作品。下达给我的创作任务是用油画表现第四野战军解放海南岛的辉煌战果。我于是去了海南搜集素材。在这个过程中,我被海南游击队在孤岛奋战二十多年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所震撼。我旋即走访了曾任海南岛游击队司令员的冯白驹,那时他是广东省副省长及广州军区副司令。 根据最感动我的情节我创作了一幅油画素描稿,还为冯白驹写生了一幅速写像,表现衣不蔽体的战士倦睡在暴风雨的树林间,冯白驹醒来凝望着织网的蜘蛛。但这幅素描后来被否了,原因是不应表现革命的低潮,不应表现失败的环节,更不应表现个别现象及个别人物。我当时就是不服,于是就改做成了雕塑送展,然后起了一个《艰苦岁月》的题目,当时全国正处在中央提出的反对地方主义的高潮中,所以我是做好了受批判的准备的。结果没想到却获了奖,这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的。 南都:一般人都以为《艰苦岁月》反映的是长征时的场景,没想到竟然说的是海南游击队的故事。 潘鹤:《艰苦岁月》为何没有受批判,我也一直很困惑,直到后来,我偶然看到《解放军画报》中有一幅描写邓小平、陈毅、彭德怀等一班统帅兴致勃勃围着《艰苦岁月》追谈往事的油画时,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可能以为表现的是长征时的艰苦岁月,引起了他们对往事的追忆。 1960年,军事博物馆成立,《艰苦岁月》被摆在了长征部分的展览,我是一直想纠正这个错误,但当时博物馆的负责人没有接纳我的意见,也不许我在外面讲这些。但世事难料,1965年,广东美术界文艺整风,《艰苦岁月》被视为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到“文化大革命”,这个雕塑从展厅被撤出,放到了一间堆满垃圾的陈列室里。 南都:你这样的性格,在“文革”中有没有被批斗得很厉害? 潘鹤:当然了。我真正创作是在后30年,前50年里,我经历了十六次逃难,三十八次政治运动,“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下放到三水劳改场放牛。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表达我当时的心态,题目是“生不逢时,千载难逢”,“生不逢时”是指我居无定所、经常逃难,而“千载难逢”是当上了文艺家,没有这些磨难和挫折,我不会有今天,正是这个困难的时期才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因此,前50年是我的艺术积累期,到后30年我才真正爆发,只有利用痛苦才能寻找艺术的爆发点,最终体味到真正的艺术。 “文革”十年,我的工作室被改成了劳改场,我跟关山月、黎雄才等六个人一起坐了一年多的牢。等到放出来后不久,又恰逢“打倒四人帮”,广州美术学院想我给学校做雕塑,我就做了一尊鲁迅。我当时想:你们这帮跳梁小丑,以前抓我的是你们,放我的也是你们,我对他们完全是不屑一顾。以前鲁迅说是“横眉冷对”,横眉冷对就把坏蛋看得很高了。但我把鲁迅的头抬很高,眼光往下瞄一瞄,意思是:你们这帮跳梁小丑,我都不屑一顾,算什么革命者,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当时是狂妄到这样子,题目就取名《睬你都傻》。 南都:你刚才说,前50年的各种经历,帮你找到了艺术的爆发点,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的风格?你会怎么来总结自己的风格? 潘鹤:风格是我人格的表达,不是金钱的表达,也不是拍马屁的表达。我的作品的风格就是,你看了可能有意见,但你也没办法打倒我。你狡猾,我比你还要厉害。这就跟人讲话是一个道理。我讲的话,你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你得提高水平,才知道我讲什么话。我经常说,这个社会上那么多坏人,做官的坏,行商的坏,你一个艺术家该怎么办?那就是比他们还要坏,坏个透,这样坏人不敢欺负我,但我要欺负你,你甚至都不知道我欺负了你。我差不多每件作品都是骂人的,但我转了很多弯,你想要打倒我,但你又找不到打倒我的理由,这就是其中的趣味。(大笑) 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国家任务 这条“开荒牛”做出来以后,反对声一片,当时甚至还有示威游行,不准摆出来。 南都:你的作品几乎都是跟政府打交道,很多甚至就是政府任务,你怎么来处理艺术和任务间的关系? 潘鹤: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国家任务,但这些任务必须要能打动我,让我能借题发挥,我才会接受。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可以说,从1970年代开始,我通过我的作品把我要讲的话全讲出来了。 我与官员的关系,就像情人一样,如果他感情很真诚,用“美人计”,那我就将计就计;但如果他特别丑,那我就走为上计;有些官员是既不漂亮又无丑样,那我就是缓兵之计。这样你才能在跟他们的交往中掌握主动。 我们和各地政府的合作,也是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最初的合同是非常坏的,首期得等到你稿子出来了才给钱,可能一百万给了你十万,然后他就拿着你的稿子找别人来做。后来我也学聪明了,你得先给我30%的首期,我才开始给你做,到第二期不给我30%,我就不铸铜,最后不给我30%我就不剪彩,那剩下的10%给不给我都无所谓了。 南都:“文革”结束之后,你很快就又提出做室外雕塑的主张,这也成为日后中国城市雕塑的滥觞,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潘鹤:早在1950年代,我就写过一系列文章批评雕塑的私人收藏,到1979年,我又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了《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一文。文章一出,立刻引起中国雕塑界的重视,当时大部分艺术家还是不能理解我,说我书生意气。因为当时各雕塑创作室内小雕塑的创作都缺经费,更何况是大雕塑。 缺钱,是当时中国雕塑面临的最大问题。当时我是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发现雕塑系的学生毕业以后很难找到工作,所以根本没人愿意报考雕塑系,整个中国的雕塑事业十分落后。过去中国的雕塑,大部分都是宗教形象,辛亥革命以后,破除迷信,各种佛像都被捣毁,大型雕塑近乎绝迹。当时的雕塑,几乎就等同于工艺品,都是做些公仔、铜像工艺品之类供出口。我是很看不起这种行为的,堂堂艺术家,就为了金钱来讨好外国人?所以我当时就提出,雕塑不能这么走,不能被外国人左右了我们的艺术前途,我们讲自己的话,而且必须是真话。 当时国家开始设立经济特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推广城市雕塑的绝佳时机。所以通过关系认识领导,游说他们用城市雕塑为城市建设服务,我劝说他们,一个城市不能只有绿化,还得有文化,但文化是无形的,如果使无形变成有形,就得靠雕塑。这样慢慢下来,就把雕塑界的需求转化成城市建设的需求。 我是从1970年代开始有大量作品,到现在,我数了数,登记在册的有六百六十件室外雕塑。 南都:你在这一阶段创作的《开荒牛》、《珠海渔女》等等,都成为代表一座城市的经典象征。你在这么短时间创作这么多作品,一般是怎样来找主题的呢? 潘鹤:我的作品都是建立在“借题发挥”基础上,再通过不断地反思、推敲,才能做出来。比如,创作深圳地标《开荒牛》之前,深圳市领导要我做一只“大鹏”,但我觉得,如果把大鹏建在市政府内,岂不就成为“笼中鸟”,我没答应;一年后,他们又提出做“莲花”,取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之意,我当时就问:淤泥是谁?你们的合作者就是淤泥吗?又一年,他们又提出做狮子,我还是反对,政府摆个“狮子”,只会让民众心生畏惧。后来他们再找我,我就提出要做一头“牛”。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与牛很有缘分,开始是只俯首甘为“孺子牛”,建国后做了“牛鬼蛇神”,现在国家又荒芜了,要重新开荒了,责任落在我们身上了,就做开荒牛。我的想法是,我做的不仅仅是一头牛,马路上千千万万推土机,都是开荒牛;开荒牛后面的树根也不是树根,是落后的意识:官僚意识、小农意识等等,它们盘根错节,如不拔了这些根,将来不会有发展。这头牛有一只前脚是跪着的,说的是这一代人鞠躬尽瘁。这些意思很多人都不懂。 这条“开荒牛”做出来以后,反对声一片,当时甚至还有示威游行,不准摆出来,我看到这个情况,也发动群众发起抗议,要保护这个雕塑。后来是,邓颖超有次来深圳,看了这个雕塑非常感动,她说开荒牛不仅是深圳特区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拔掉穷根、埋头苦干。这才让开荒牛留到了现在,逐渐深入人心。 在《开荒牛》之后,我又做了一个《艰苦岁月》,提醒深圳人民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岁月。又过了几年,我觉得得提醒大家不要得意忘形,还得自我完善,于是我就又做了一个《自我完善》。可是到现在,深圳都不愿意把这个雕塑跟其他两个放到一起,领导说:“难道现在不完善吗?”现在《自我完善》这个雕塑还摆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公园”门口。 室外雕塑乱象 现在很多雕塑不知所谓,有些所谓的艺术家更是完完全全变成了奸商。 南都:海珠广场上的《广州解放纪念像》也被人反对过吗? 潘鹤:也被人骂了,我几乎每个作品都会有人骂。在现在的海珠广场这个地方,原来就有一个雕塑,穿着苏军的服装。“文化大革命”前,他们觉得这个雕塑是暗示苏军占领广州,所以最后给毁掉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群众希望能重新做一个,于是就开始了全国征稿。 当时大概投来了10万多份稿子,这些稿子,几乎都是把国民党的党旗踩在地上,这似乎成了一个默认的格式。但我不认可这种做法,我当时有一个想法,但不好讲,就是国共过去毕竟合作过,世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是分,明天说不定就合了,你今天踩着国民党旗,明天要是和好了那该怎么办呢? 其他设计者都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我想到了,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不能这样做。现在我做的这个,就把脚踩的国民党党旗换成了鲜花,这些花是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时抛过来的。然后我还在雕塑底座刻了几个大字———“一切政权属于人民”,这样就把党派的色彩淡化了。 我的每件作品,我都会考虑它们在我死后可能会有的遭遇,在成百上千年之后,它们不仅还能存在,同时还能让别人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这样希望的。 南都:雕塑给你带来这么多快乐,但为什么当初你并不希望你儿子潘奋继续做雕塑? 潘鹤:因为在我们那一代做雕塑是艰苦而又贫穷的艺术,而且也很危险,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最好不要从事雕塑。雕塑做好了得摆在公众场所,但我们对公众场所没有话事权,必须得听领导的。这时就有一个问题了,领导的话你到底听不听,如果你不听,那你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他们这代人没有我这种能力,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哪怕枪毙我,我都觉得很光荣。现在不是这样,很多雕塑不知所谓,有些所谓的艺术家更是完完全全变成了奸商。这就是现在的大背景,谁也没办法。 南都: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潘鹤:现在不能站,以前腰椎间盘突出,刷牙都不可以。后来腰椎、大腿、小腿出问题都医好了,就是站不稳。不过我很乐观的,我都九十岁了,贪得无厌是不行的,“贪”字多一点就变“贫”了。当年我和关山月从牛棚里面放出来,我找一个地方做工作室,关山月给我题了“云鹤楼”的匾,赖少其给我写对联“云往云来浮沉无意,鹤翔鹤立宠辱在望”。这副对联在我工作室摆了五六年了,但我后来发现我们还是太天真了,世界哪有这么简单。于是我就把它们都取下来了,让杨善深给我重新写“戆居居”的匾,意思就是没有脑筋的人,表示我是一个很蠢的人。后来杨善深又给我写对联“能受天磨真好汉,不招人妒是庸才”。 南都:从你在1970年代提出雕塑走向室外以来,现在城市雕塑越来越多,但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经常会有非常“雷人”的作品出现。在你看来,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潘鹤:自从我提出“雕塑要走向室外”开始被大家所接受以后,现在越来越多雕塑走向室外,在1970年代以后,可以说中国出现了千千万万的雕塑。但也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 1980年代,我跟刘开渠成立了雕塑学会,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刘开渠有一次找我,说北京一条马路有几十件雕塑,水平很差,摆在那里很难看,问我怎么办。他提出来全部撤走,搬走它们。但我的意思是,搬走是没问题,但仔细想想却非常麻烦:如果不搬走,我们两个就是名誉扫地;搬走,我们就是在浪费国家财产。而且就算我们搬走了这批雕塑,但也根本打击不到那帮在做这样雕塑的人,他们大可挪去其他省份继续做。而且我们这样做,不仅打击不了水平低下的“艺术家”,反而会打击到官员,让他们以后不敢再随便答应做雕塑。 所以这件事情弄得我们非常头疼,我们一开始两个人带头成立雕塑学会,想的是可以流芳百世。结果现在这些户外雕塑这么差,不三不四的艺术家得意忘形,都抢着做这些雕塑,做出来的也是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最后我们两个发起人,可能就会遗臭万年了。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我们这一代人也是没有办法。 |